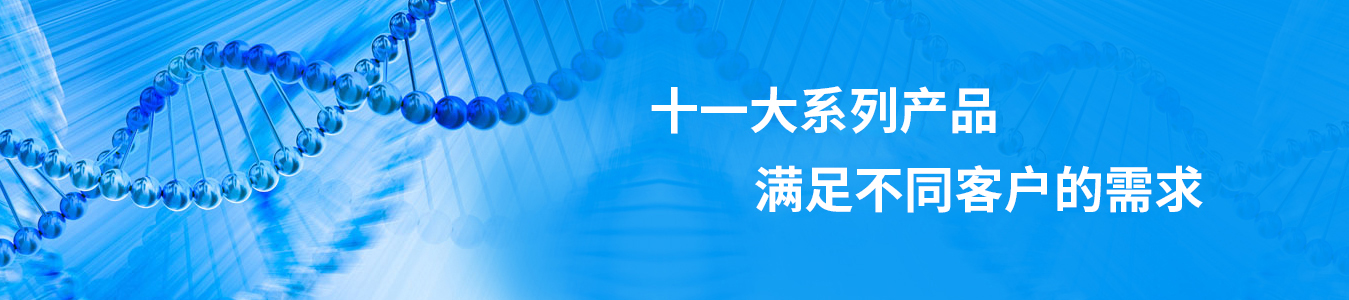【佳学基因检测】感染性疾病发生的个体基因决定因素
多细胞真核生物在进化后期从病毒、细菌、古细菌和单细胞真核生物的海洋中崛起,这些大型生物与各种微生物接触并被感染。足够大的生物体甚至可能受到多细胞真菌和寄生虫的侵扰。每次相互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发生在两个独特的生物体之间,且每种情况都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一现象在临床上表现为感染的个体之间变异性极大,即使是对于同一种病原体,也可以从无症状到致命。佳学基因检测研究并形成了一种观点,即人类的致命传染病可能与个体单基因的先天免疫缺陷有关,这些缺陷通常不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律,并且常常表现出不完全的外显率。人体被感染的风险的基因解码基因检测回顾了近二十年里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尤其是一些《人类遗传学》上发表的详尽评论。几乎所有致命的传染病都有可能由某种单基因缺陷引起,尽管这些缺陷可能与免疫系统有关。尽管单基因病例的比例仍不明确,但研究揭示了遗传异质性与生理同质性结合的现象,可能初步揭示了人类严重传染病的遗传结构。
介绍
人类群体中,微生物引发的良性和危及生命的感染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微生物间的变异现象显而易见,且容易理解,因为它看似主要由微生物的毒力决定,与人类群体的差异无关。毒力是《人体基因序列变化与人体疾病表征》上面的一个专有名词,旨在量化微生物对人群的影响,虽然大多数微生物的毒力分子基础尚不清晰,但它具有普遍适用性。例如,埃博拉病毒比单纯疱疹病毒的毒性要强,因为埃博拉病毒在自然条件下的致死率为60%左右,而单纯疱疹病毒的致死率不到0.01%。但这些比例可能随着时间和微生物与宿主的共同进化而发生变化。例如,埃博拉病毒可能在与人类共同进化数百年后,其毒性逐渐减弱;而单纯疱疹病毒的祖先可能曾更具毒性,并且古代人类更易感染这种病毒。此外,微生物对不同人群的危害也会因不同的生态环境和进化事件而有所不同。因此,所有微生物都可以在某些时间和空间内按毒性从无害到致命排序。
单个微生物与个体人类
这种微生物变异的分析促使人们提出了致命性与机会性感染的二元概念,试图将微生物分为两类:一类足够毒性强,能够在“免疫功能正常”的个体中引起严重疾病;另一类仅在“免疫功能低下”的个体中造成严重疾病。然而,现实远比这种二分法复杂,因为微生物的致死率几乎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难以将它们简单地分为两类。此外,这种二分法逻辑上也不成立,因为任何患有危及生命的传染病的人,实际上都表现出免疫功能的缺失。将“免疫缺陷”仅限于检测出的免疫异常显然不合适,因为检测方法和异常的实际含义也在不断发展。这些简化的概念虽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不能准确描述人类感染的复杂性,尤其是它们没有考虑人类群体与微生物群体的互动结果。实际上,没有通用的“宿主”或“病原体”,只有独特的个体和微生物群体。
每个人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是独特的
每个人与微生物的互动都是独一无二的。感染发生在具体的个体与特定微生物接触时,而非在理论上的人类物种与微生物物种之间发生。虽然人类物种的定义在进化上很困难,但从生理角度来说并不复杂。而微生物物种的定义则更加复杂。此外,生命的延续本质上与个体有关,不仅是群体的事情。每个生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表现都是独特的,这一观点正是达尔文和伯纳德的进化和生理学理论的核心,也是生命科学与物理学的根本区别。在进化和生理学的背景下,个体差异是不可忽视的。人类体内的每个细胞在遗传和表观遗传上都会有所不同,因此身体从未被单一微生物感染。相反,身体内可能会同时存在多种微生物,而这些微生物又会进一步进化、变异和分化,增加了更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巨大的个体差异
这种独特的互动方式使得感染的临床表现差异极大,从无症状到致命性疾病。最具毒性的微生物对一些人可能是无害的,而最不具毒性的微生物却可能致命,尽管这种情况较为少见。这就是“感染之谜”的所在。在感染过程中,临床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微生物本身的变异、宿主的差异或其他外部因素(如入侵微生物的数量或传播途径)造成的。这些因素已经在临床研究和实验模型中得到证实。例如,皮肤破损后的葡萄球菌感染和创伤性脑脊液漏引起的脑膜炎都可以影响感染的结果。微生物接种量也极为重要,这在动物模型的实验感染中有广泛验证。
微生物毒力的作用
微生物种群内的变异偶尔能解释毒性较强的微生物株出现的原因。例如,季节性流感病毒与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的区别,前者通过基因漂变形成毒性变化小的流行株,而后者通过基因转移形成毒性较大的流行株。虽然这些研究揭示了微生物毒力的多样性,但它们通常假设人类群体是同质的,忽视了个体间的差异。这种忽略可能导致对流感等病毒的研究不够全面,特别是对不同个体的反应差异没有足够的关注。
获得性免疫缺陷的作用
获得性免疫缺陷也对感染的易感性产生重要影响,最常见的例子包括麻疹和艾滋病毒(HIV)感染,这些病毒会导致免疫系统受损。免疫抑制药物,尤其是免疫抑制治疗,也被认为是感染易感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还有许多未知的获得性免疫缺陷形式,可能与体细胞基因突变或表观遗传修饰相关,这些缺陷可能导致与衰老相关的免疫功能下降。带状疱疹便是一个例子,这种疾病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再激活引起,通常出现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
原发性感染的重大影响
然而,我们不讨论人类在继发性或再激活感染中的基因控制,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继发性或潜伏性感染的结果通常受到适应性免疫系统的显著影响。适应性免疫系统在进化过程中通过趋同进化独立出现了两次。尽管其受到基因控制,但该系统及其赋予的免疫力通过体细胞重排产生抗原受体,与种系分开。在继发性感染中,适应性免疫系统通过对先前感染的记忆提供增强的免疫力,这本质上是一个体细胞过程。需要重申的是,我们并不是说这一过程不受种系遗传控制,但我们认为,与原发性感染相比,种系和体细胞变异对继发性感染结果的影响更加复杂。其次,从生理和进化的角度来看,微生物威胁对人类和其他物种构成的根本挑战,更多来自原发性感染而非继发性感染。在人类中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自然条件下,缺乏或几乎没有医疗保健的人类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至少维持在20到25岁,且在10,000年内几乎没有变化,直到19世纪末。一半的儿童在15岁之前死亡,且大多数死于原发性感染,而非战斗、战争或饥荒。现代人类寿命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卫生、无菌手术、血清疗法、疫苗接种和抗感染药物的进步,这些进步紧随细菌学理论而来。现代人类的适应性免疫反应从50岁左右开始对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的效力逐渐减弱,这无疑是2020年的一个重大医学问题,但从进化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次要的生物学问题,因为它发生在晚期,对生殖的影响微乎其微。
人类遗传假说
因此,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进化和生理问题是:为什么许多儿童因感染死亡?鉴于大多数儿童(包括死者的亲属)在感染相同或相关微生物后能够幸存且没有严重后果,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人类遗传假说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而提出,并通过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遗传学得到了证实。我们在其他地方回顾了这一领域的历史。简而言之,生物统计学家和遗传学家从1905年开始为植物,1923年为动物,以及1909至1943年期间为人类提供了有关严重感染可能具有遗传起源的原理证据。植物生物学家通过研究小麦真菌感染,首次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严重感染可能是遗传的,甚至是孟德尔遗传的。然而,巴斯德本人也证实,蚕的两种感染之一——软化病,属于“遗传”的,不是指微生物从父母传给后代,而是后代继承了父母的感染倾向。巴斯德虽然没有意识到孟德尔遗传定律,也未朝这个方向开展研究。植物感染的遗传成分后来成为弗洛尔于1942年提出的一般模型。多项研究证实了遗传背景对动物感染结果的重要性,包括小鼠、大鼠、兔子和豚鼠的研究。在人类中,从1909年到1940年代,研究者采用了多种流行病学和临床遗传学方法,其中最具影响力且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是双胞胎研究,通过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对特定表型的一致性。后来,还进行了同样有效的过继研究。
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各自贡献
有趣的是,免疫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并未解决原发性感染过程中个体临床表现的差异性问题。这一点值得简要说明。微生物学家通常将微生物视为病因,因此认为个体间的临床差异是由于某种形式的微生物变异,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的。尽管如今绝大多数病原体杀死的感染者不到1%,微生物学家通常将疾病和死亡归因于微生物,尽管他们并未记录哪些具体的微生物变异导致了特定患者的发病或死亡。免疫学家在这方面是另一种历史学说的继承者。许多人不愿承认,免疫系统即便在群体层面有效,在个体层面却可能无效。大多数免疫学家依然不承认,至少某些人群可能对特定微生物存在免疫缺陷,尽管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有很强的说服力。这种情况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在1917年,许多免疫学家放弃了对感染免疫的研究,因为兰德斯坦纳发现抗体对半抗原(即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合成分子)反应的现象震惊了他们。免疫学家一直专注于Kindt和Capra提出的“抗体之谜”,这与感染之谜有所不同(Kindt和Capra,1984年)。微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对解决这一问题不感兴趣,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植物、动物和人类遗传学家的第三个学术群体决定着手解决感染之谜。
临床和群体遗传学
快进到20世纪50年代初,人类传染病遗传学从传统遗传学转向了分子遗传学。在接下来的60年中,该领域继续分为两个分支:临床遗传学家和群体遗传学家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尽管他们研究的是相同的问题,但提出了不同的假设,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描述患者的表型和分析其基因型。群体遗传学家通过人群研究进行分析,较少关注详细的临床表型、家族史和疾病机制。他们对人类遗传变异进行基因分型,并将其作为标记进行分析,而不是候选的致病变异。相对而言,临床遗传学家则进行以患者或家庭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更加精细,开展详细的临床研究,直接寻找候选的致病突变,并试图破译疾病机制。从事后看来,毫无疑问,在1950年至2010年期间,临床遗传学相较群体遗传学更为信息丰富。传染病群体遗传学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仍然是1954年发现的HbS性状,该性状可使个体对严重的恶性疟原虫疟疾具有十倍的抵抗力,这一发现标志着该领域的诞生。后续的群体研究并未发现如此高的遗传保护或易感性,即使这些研究揭示了IL28B变异在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清除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严重疟疾的十倍抗性更多的是告诉我们,严重感染对人类遗传变异分布的影响(如疟疾选择了HbS等位基因),而不是人类基因型与严重感染之间的因果关系(HbS杂合子未能完全免受疟疾侵害)。
感染易感性/抵抗力的“孟德尔”基础
到2010年为止,已有基因解码指出至少200种先天性免疫缺陷和3种孟德尔感染抗性。这一领域的起源可追溯到1946年,当时发现常染色体隐性疣状表皮发育不良,尽管这一领域的起步常被归因于1952年发现的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和1950年发现的常染色体隐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自此,相关研究揭示了许多由先天免疫缺陷引起的传染病案例。该领域的核心概念是克劳德·伯纳德的决定论,与群体遗传学家常用的易感性概念有所不同。1996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科学家首次发现了孟德尔抗性及其对应特定传染病易感性的分子遗传基础:对HIV感染的抗性和对弱毒性分枝杆菌的易感性。CCR5缺陷导致的CD4+ T细胞对HIV的抗性,受到1976年关于抗间日疟原虫个体红细胞缺乏Duffy抗原研究的启发。然而,直到1995年,才通过DARC启动子中一个细微突变的发现,确定了这一表型的分子遗传基础。特定健康患者中所发现的“特发性”分枝杆菌感染的孟德尔基础尤为令人惊讶,因为它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描述的其他原发性免疫缺陷的发现相矛盾,这些免疫缺陷通常伴随免疫异常和多种感染。孟德尔分枝杆菌病易感性(MSMD)被证实是由IFN-γ免疫的先天性错误引起的。寻找“孟德尔感染”分子基础的启示,来源于1986年和1993年发现的小鼠特定感染的单基因病变,如Mx和Nramp1,以及植物领域的相关研究。
传染病的单基因基础
自1946年起,只有5种严重的人类传染病被证实具有孟德尔遗传性,且往往在家族中呈现遗传性(见表1)。这些疾病的分子遗传基础于1996年被揭示,证实其孟德尔遗传特性。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传染病并非孟德尔遗传。然而,迄今为止研究的所有传染病中,至少在一个儿童身上已证明它们是单基因病。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和寄生虫病在内,超过15种人类感染属于这一类(见表1)。这些感染的标志之一是遗传异质性,包括基因座和等位基因异质性。而这些感染在生理上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例如,MSMD是由IFN-γ免疫的先天性缺陷引起的,已知涉及15种基因和30种等位基因突变;慢性粘膜皮肤念珠菌病(CMC)则是由IL-17A/F免疫的先天性缺陷引起的,涉及10种基因和11种等位基因突变。随着下一代测序技术(NGS)的应用,遗传异质性和生理同质性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10年成为另一个转折点,因为NGS使临床遗传学和群体遗传学家能够使用相同的遗传数据,显著拉近了这两个领域的距离。得益于这种联合研究方法,关于严重传染病背后单基因病变的研究蓬勃发展。例如,人群研究发现P1104A TYK2等位基因的纯合性是结核病易感性的一个因素。然而,我们并不是说所有新的遗传病因都能轻易与已知病因在生理上联系起来。例如,SNORA31突变被认为是单纯疱疹性脑炎的病因,但它似乎与TLR3通路中的突变无关。这项工作可能需要时间去解决,正如解开一个巨大的拼图。然而,我们有理由预测,对于每种严重的传染病,必定存在一个对应的、最终能被解开的分子谜题。
表 1.孟德尔和单基因感染易感性/抗性
| 感染因子 | 临床表型 | 免疫表型 | 基因 | 遗传性 |
|---|---|---|---|---|
| BCG疫苗和环境分枝杆菌 | MSMD | IFN-γ 缺乏 | IFNGR1、IFNGR2、IL12RB1、IL12B、NEMO、STAT1、CYBB、IRF8、ISG15、TYK2、RORC、IL12RB2、IL23R、SPPL2A、JAK1 |
孟德尔或单基因 AR、AD、XR |
| 结核分枝杆菌 | 结核病 | IFN-γ 缺乏 | IL12RB1, TYK2 |
单基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奈瑟氏菌 | 侵袭性疾病 | 补体缺乏 | C5、C6、C7、C8A、C8B、C9、CFB、CFD、CFP |
单基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XR |
| 荚膜化脓性细菌 | 侵袭性疾病 | 补体缺乏 | C1QA、C1QB、C1QC、C1S、C2、C3、C4A、C4B、CFH、CFI |
单基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肺炎链球菌 | 侵袭性疾病 | TIR 反应缺陷 | IRAK4, MYD88, NEMO, HOIL1, HOIP, RPSA |
单基因 AR、AD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复发性疾病 | TLR2 反应缺陷或 IL-6 缺陷 | TIRAP、IL6RA、ZNF341、STAT3、IL6ST e |
孟德尔或单基因 AR、AD |
| 惠普尔养育苗 | 惠普尔病 | IRF4 缺乏症 | 干扰素因子4 |
单基因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
| EB病毒 | X连锁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严重感染;B细胞淋巴瘤 | 细胞毒性 T/NK 细胞缺乏 | SH2D1A、XIAP、CD27、CD70、ITK、TNFRSF9、MAGT1 |
孟德尔或单基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XR |
| 人乳头状瘤病毒 |
疣状表皮发育不良 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病 |
EVER-CIB1 缺乏症 NLRP1 功能增益 (GOF) |
EVER1, EVER2, CIB1
NLRP1 |
孟德尔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单基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单纯疱疹病毒 (HSV) | 前脑脑炎 | TLR3-IFN-α/β 缺乏症 | UNC93B,TLR3,TRAF3,TRIF,TBK1,IRF3 |
单基因 AR、AD |
| snoRNA31 缺乏症 | SNORA31 |
单基因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
||
| HSV、流感等 | 脑干脑炎 | DBR1 缺乏症 | DBR1 |
孟德尔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流感 | 重症流感 | I 型和 III 型干扰素缺乏症 | IRF7、IRF9、TLR3 |
单基因 AR、AD |
| 巨细胞病毒(CMV) | 致命感染 | NOS2 缺乏 | 一氧化氮合酶2 | 孟德尔AR |
| 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 复发性/严重感染 | MDA5 缺乏 | IFIH1 |
单基因 AR、AD |
| 人类疱疹病毒 8 | 卡波西肉瘤 | OX40 缺乏 | OX40 |
单基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甲型肝炎病毒 | 暴发性肝炎 | IL18BP 缺乏症 | IL18结合蛋白 |
单基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麻疹和黄热病活疫苗 | 严重感染 | IFN-α/β 反应缺陷 | 干扰素受体1、干扰素受体2、STAT1、STAT2 |
单基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念珠菌 | 羧甲基纤维素钠 | IL-17 缺乏 | IL17F,IL17RA,IL17RC,TRAP3IP2,STAT1,JNK1 |
孟德尔 AR、AD |
| 皮肤癣菌 | 侵袭性皮肤癣菌病 | CARD9 缺乏症 | CARD9 |
孟德尔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伊氏锥虫 | 锥虫病 | APOL1 缺乏症 | 载脂蛋白1 |
单基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间日疟原虫 | 抵抗感染 | 红细胞中缺乏病原体受体 | 达卡雷尔 |
孟德尔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 | 抵抗感染 | CD4 + T 细胞缺乏病原体受体 | CCR5 |
孟德尔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 诺如病毒 | 抵抗感染 | 肠道上皮缺乏病原体受体 | FUT2 |
孟德尔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
a我们将具有完全临床外显率的单基因疾病称为孟德尔疾病,将具有不完全临床外显率的单基因疾病称为单基因疾病
b AR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AD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XR 为X 连锁隐性遗传
c我们仅列出在两名或两名以上结核病患者中发现突变的基因。大多数 MSMD 致病基因也是结核病的罕见遗传病因。我们没有指出等位基因形式之间的任何差异。这对于TYK2尤其重要,因为功能丧失 (LOF) 变异的纯合性是结核病的罕见病因,而 P1104A 等位基因的纯合性在一般人群中很常见,可能占欧洲血统人类结核病病例的约 1%
d RPSA的变异是孤立性先天性无脾症的基础
STAT3、ZNF341和IL6ST的变体是葡萄球菌病和其他一些感染的根源
人类传染病遗传学:何去何从?
这些研究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位于临床和群体遗传学的交叉点。首先,这种单基因病变模型(通常表现为不完全外显率、遗传异质性和生理同质性)是否适用于所有严重感染?迄今为止研究的所有感染中,至少在一名患者中已发现是单基因的,但这是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感染,无论是罕见的还是常见的?其次,是否只有罕见的遗传病因,占常见感染的一小部分(且可以说罕见感染的比例更高)?最近发现,TYK2 P1104A纯合突变是结核病的常见隐性病因,这表明单基因(但非孟德尔)感染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更为常见。对于任何特定感染,包括常见感染,单基因形式的比例是多少?第三,不完全外显率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不同的感染已被证明与等位基因相关,且相同的等位基因在不同患者中可能引发不同类型的感染,例如,单纯疱疹性脑炎和流感肺炎似乎都是由TLR3突变引起的,但影响的患者群体不同。遗传修饰因素可能在此发挥作用,尽管微生物的数量和感染途径等因素也可能是关键。感染易感性还可能存在双基因或寡基因形式。大规模的基于人群的研究有助于解决这三个问题。例如,SARS-CoV-2疫情促成了COVID-19人类遗传学研究(COVID-19人类遗传学),这是一个国际联盟,旨在分析曾经健康且相对年轻(<50岁)的患者中危及生命的COVID-19的遗传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单基因抗感染研究逐步发展,但与单基因易感性研究相比,其发展速度和范围相对较慢。三个引人注目的耐药性病例分别出现在1976年、1996年和2003年,涉及间日疟原虫感染(Miller 等人,1976年)、HIV感染(Dean 等人,1996年;Liu 等人,1996年;Samson 等人,1996年)和诺如病毒感染(Lindesmith 等人,2003年)。而对间日疟原虫的耐药性基因损伤直到1995年才被描述(Tournamille 等人,1995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一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有一小部分人类对一些非常常见的病原体具有完全的自然免疫,这已通过阴性血清学检测得以证实。
临床意义
许多严重感染可能具有单基因基础,且具有不完全外显率和遗传异质性,但在某些患者中表现出生理同质性,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生物学意义。从临床角度看,这些发现为患者提供了分子诊断,并为家属的遗传咨询提供了可能性。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总是对临床有益的,哪怕并非能立刻加速诊断过程。这为通过恢复免疫功能的预防或治疗方法提供了基础。例如,由遗传性细胞因子缺陷引起的感染,最好通过相应的重组细胞因子或由该细胞因子调控的关键产物来预防或治疗。最好的例子是使用重组IFN-γ治疗那些因基因缺陷无法产生IFN-γ的患者(Alangari 等人,2011年;Holland,2001年)。此外,阐明罕见单基因病例中传染病的发病机制还可以揭示在更常见患者中(例如HIV感染者)的作用机制(Zhang 等人,2017年)。最后,疫苗开发也将从这种研究方法中受益,因为疫苗的目的是保护那些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而自然免疫力强的个体则无需接种疫苗,并且可能是任何临床试验中的主要干扰因素(Glass 等人,2012年)。这些研究的生物学意义也不容忽视。遗传缺陷揭示了相应基因的冗余和非冗余作用,以及这些作用在生态和进化选择中的功能(Barreiro 和 Quintana-Murci,2010年;Quintana-Murci,2019年;Quintana-Murci 和 Clark,2013年)。这些研究为自然免疫力的定义提供了基础(Quintana-Murci 等人,2007年)。这与在动物疾病模型下进行的实验性感染研究相对照,形成了对比和补充(Casanova 和 Abel,2004年;Fortin 等人,2007年;Quintana-Murci 等人,2007年)。此类研究还定义了人类基因的冗余程度:冗余度低的基因突变后可能导致多种感染;冗余度高的基因突变后通常仅会导致一种或几种感染;完全冗余的基因不会引发任何感染表型;而具有有益冗余的基因突变则可能产生对一种或多种感染的抵抗作用(Casanova 和 Abel,2018年)。
生物学意义
该领域的生物学意义显而易见,或许比临床意义更为突出。实际上,通过人类遗传学的方法研究自然免疫力已推翻了许多免疫学的传统观念(Casanova 等人,2013年)。例如,TLR3和IL-1R以外的TLR曾被认为对宿主防御各种传染性病原体至关重要。然而,IRAK4和MyD88缺陷的发现表明,这些基因对宿主防御肺炎球菌和葡萄球菌至关重要,但在其他方面几乎是多余的(Casanova 等人,2011年;Ku 等人,2007年;Picard 等人,2003年;von Bernuth 等人,2008年、2012年)。这一方法还揭示了除白细胞外,其他细胞在免疫反应中的作用(Zhang 等人,2019年)。例如,TLR3突变被证明是单纯疱疹病毒脑炎和流感肺炎的根本原因,其机制不是破坏白细胞免疫,而是损害皮质神经元和肺上皮细胞的病毒内在免疫(Casanova 等人,2011年;Casrouge 等人,2006年;Lafaille 等人,2012年;Lim 等人,2019年;Zhang 等人,2007年;Zimmer 等人,2018年)。这些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与免疫学的传统预测存在矛盾,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远远超出了本章的范围。可以说,研究发现,自然条件下对感染的免疫力比以往预期的具有更高的冗余度(Casanova 和 Abel,2018年)。先天性免疫缺陷对特定感染的特异性并非源于特定分子相互作用,正如大多数免疫学特异性那样。相反,它反映了宿主防御基因缺陷的广泛冗余性,临床上仅表现为保护性免疫的缺陷。这些缺陷可以被视为感染的先天性免疫缺陷。